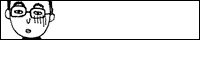近年來,台灣有越來越多的紀錄片在觀眾心中引起巨大迴響,過去被視為票房毒藥的記錄片紛紛繳出卓越的票房成績,甚至引發國際間的討論及廣大注意。
紀錄片導演用作品宣示以小搏大的決心,不畏強權只為宣揚自我理念。
2004迄今有多部紀錄片成為熱門話題,除了得獎紀錄,其票房也甚是可觀,並且相繼獲得各界名人的推薦,引發各種延伸討論。這幾部紀錄片分別為全景工作室拍 攝於921震災的七部紀錄片《生命》、《部落之音》、《梅子》、《三叉坑》、《在中寮相遇》、《天下第一家》、《再見長寮尾》,並推出2004年秋天大賞 《全景映像季》,《生命》紀錄從921地震事件中生命的痛苦轉而為重新出發的生活動力;之後關於WTO進口稻米的紀錄片《無米樂》表現出農民的辛苦,映照其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,該片也在各大新聞媒體出現熱烈討論;《翻滾吧!男孩》生動表現出師生為了奪取金牌的夢想而苦練體操的奮力向上;《奇蹟的夏天》紀錄一群東部孩子的青春,從人生邊緣的無趣與失落,透過體育班的淬練終能找回自我成就的歷程,一路過關斬將的勝利光榮,成為青春最重要的記憶。
曾 幾何時,紀錄片在台灣也開始成為熱門話題並蔚為風潮,不再是電影院的拒絕往來戶,大家開始買票進入電影院觀賞及付出關懷,盛況空前。然而,盛況之後,是否 為社會帶來更多的省思與改革力量?從這幾部片子可觀查出,台灣紀錄片重視的是深深根植在這片土地上,在台灣人共同的生命經驗中,散發著台灣生命力的。台灣 的紀錄片發展,不乏對政治議題、社會運動及人文生活的關注,小衆媒體將其關懷付諸影像,然卻依舊只是小衆媒體,影片的能見度並不高。而這些影片大多透過影 展來宣傳,無法成為社會大眾熱烈關注與反省的焦點,十分可惜!台灣不是沒有好的紀錄片,但除了《生命》、《翻滾吧!男孩》以網路部落格書寫形式和透過獲獎 的肯定稍稍拓展了群眾討論之外,台灣紀錄片語觀眾間的互動與迴響,始終僅限於小衆,而不為廣泛社會大眾所熱衷......
除了上述幾部較為人知的紀錄片外,一直以來,仍有不少影像紀錄者拍攝出撼動人心的紀錄影片。以"反省島國現況"的課題,陸續完成關懷離島的影片如2000年完成的《流離倒影》系列,結合了12位台灣優秀的獨立製片工作者分別拍攝了【浮球、西嶼坪、0304、輻射將至、馬祖舞影、噤聲三角、鄉愁對話錄、我的綠島、基隆嶼的青春紀事、誰來釣魚R、南之島之男之島、清文不在家】等紀錄片。
膠捲往往取代了現實,構成我們的地方意識......
《流離倒影》系列的影像工作者自費籌拍在台灣發展史上向來被冷落的邊陲離島,因此 可以不受任何官方意識形態的干擾而自由發揮,有效利用紀錄片美學或知識論來呈現「地方」的真實性。然而,影像再現的機制必會受到社會意識形態的滲透,那 麼,又以影片本身來說明影片帶來不同的詮釋空間,卻似乎又前後矛盾了。因此,在地空間的「形象」單憑紀錄片就能重新傳達、顛覆,或具有代表地方聲音的權 利?我想進一步思考的是,真實既然不能被複製,那藉由鏡頭所呈現出來的地方文化自然也僅只是全部現象的一角,不足以為該地方文化的全部。
紀錄片是非劇情的,具歷史和真實性的,以至於被認定為具客觀性的。但弔詭的是,紀 錄片卻又具有宣教、誘導、思考和行動的功能。藉由人物在鏡頭前的展演來達到說服性,是紀錄片創作上的突破,也是影像工作者越趨誠實的面對自我觀點姿態的展 現,更嚴然成為紀錄片拍攝的主要模式。我想,越來越多的對「虛構和非虛構」、「創作」與「紀錄」界線的任意模糊,已經逾越了我們對紀錄片理論問題的探討, 而轉變為一種「道德」性的問題了......
透過詮釋「地方」的紀錄影片,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這些影片中所關乎「異質」文化的 揭露,因為這些影片滿足了主流文化的觀眾「觀賞的慾望」,讓觀眾得以一窺其他文化「奇觀」的究竟。但是,真正的問題是,以「外來者」(例如我們的NGO組 織或導演)的身份侵入異文化中拍攝其「奇觀」,是否會引來更多複雜的問題?
去年我們的工作團隊先後為部落拍攝了兩部紀錄片《展望山興未來》、《達悟主任》,雖都是 小成本的短片,卻讓我們強烈感受到,當原住民文化的儀式轉變為一種展演,異質文化在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同質文化中顯得珍貴而與眾不同。樂觀的態度來看,也許 透過這樣的形式展現,可以讓原住民重拾對自我的認同,為保存自身文化盡一份心力,並且因此凝聚意識發展部落,換取更好的生活品質。
如今,我們將再籌拍一部紀錄影片,關於花蓮縣富里鄉的達蘭埠部落在六十石山栽種金 針的故事。歷經數月密集的會議與宿醉的生活融入,而我們所扮演的角色只是秉持客觀原則的旁白,不會是主角。期待能透過紀錄片呈現部落某程度想改變現況的渴 望,活絡原鄉的生命力,實踐我們進行社會參與的決心。